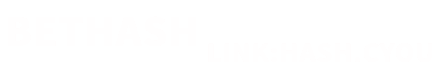
HASHKFK
BETHASH官方网站(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林黛玉是林家来的孤女,贾府只管照顾她的生活,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一直缺少一个能引导她的人,虽然有宝玉的陪伴,但这种无所依怙的孤独感是没有办法消除的。而宝钗有母兄在侧,在京中也有自己的族产,一举一动又是那样的随分从时。对孤女黛玉来说,这在无形中加剧了她内心的不安。小说对黛玉儿时这些尖刻语言的描写,是在突出她作为“草木之人”的性格特质。她寄人篱下的孤女处境,性格中的敏感多疑、率真自然,都在这些尖锐言辞中得到了“不写之写”。
两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宝钗与乐羊子妻的“停机德”代表了儒家礼教文化,黛玉和谢道韫的“咏絮才”体现的则是魏晋风度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两种价值观刚好是相对立的。“停机德”与“咏絮才”的对比可以上溯到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其中就说到谢道韫“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而张玄之妹则“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林下风气”是说谢道韫像竹林七贤这些隐士一样具有魏晋风度,不为世俗拘束,而“闺房之秀”则是说女子贤良,能安家室。
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并举不仅成为一种固定模式,而且这两种类型的女子还总是“联袂登场”,甚至在社会评价标准中,人们会主张这两种品质应当合二为一。乾隆年间推出过一部大书叫作《石渠宝笈》,其中收有永乐年间名臣姚广孝的一篇跋文,题在赵孟的夫人管道昇画的《碧琅庵图》上,说“天地灵敏之气,钟于闺秀者为奇”,还说管道昇“真闺中之秀,飘飘乎有林下风气者欤”,将这两种代表不同女性之美的特质合二为一,提出既要做“闺中之秀”,也要有“林下风气”,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评价女性的词——“兼美”。
“兼美”这个词在《红楼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他,这位女子“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乳名兼美字可卿”。“兼美”一词呼应了判词中的“停机德”“咏絮才”,所指向的是“清心玉映”“神情散朗”合二为一的特征。明清时期,用这种“兼美”的形象来塑造“双女主”的才子佳人小说不乏其例。清代还有一部很流行的小说《平山冷燕》也用到了这种设计,其中的两位女主角分别叫山黛、冷绛雪,才美俱在伯仲之间,曹雪芹给自己小说中的女主角起名叫林黛玉、薛宝钗,或许也是受到这本小说的影响。
从这种视角来看,我们无须比较钗黛之间的优劣,因为她们的品格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赞扬、所高标的。无论是乐羊子妻还是谢道韫,都契合于《红楼梦》“使闺阁昭传”的标准。作为女子,她们都有非常壮烈的事迹,比丈夫更深明大义,追求更高远。乐羊子妻在丈夫游学期间,面对闯入家中的盗贼,最终刎颈自尽,以保清白,死后被太守追赠“贞义”的谥号;谢道韫后来嫁给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在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之乱中,面对丈夫、儿子都被杀害的惨况,她临危不惧,与婢女抽刀出门,挺身迎敌,手刃数人。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宝钗和黛玉身上不仅体现着道德操守和风流才华,还有着共同的女性担当,这也是曹雪芹为二卿合传的原因所在。
在贾母面前,她是时时逗人开心的孙媳妇,常常用“反话正说”的方式来调节气氛。气氛欢快的时候,她的话往往能锦上添花。比如在第三十八回中,贾母说起自己儿时掉进水里,鬓角被木钉撞出一个窝儿时,未等众人接话,凤姐便将贾母比作老寿星,“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而当场面尴尬、气氛凝重时,凤姐也能以三言两语化解尴尬,缓和气氛。在第四十六回中,贾母因为贾赦要纳鸳鸯为妾而“气的浑身乱战”,李纨早就带着姊妹们退了出去,王夫人被错怪,并不敢辩解一句。在这样尴尬的时刻,凤姐剑走偏锋,支派起老太太的不是来。她笑道:“谁教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贾母顺势要把鸳鸯赐给贾琏。这时,凤姐的反应更快了:“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一来一往,现场剑拔弩张的气氛立刻就松弛下来,贾母的怒气也消了一半。
凤姐不仅善于逢迎长辈,也会细心照顾平辈和晚辈的感受。林黛玉进贾府时,凤姐充分展示了她的语言艺术。凤姐来时,头一句说的是:“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既带着歉意,又自彰身份,语气中更兼调侃,缓解了初来乍到的黛玉生疏和局促的情绪。后面的一番话更是面面俱到,照顾到了在场的每个人。她先夸黛玉的容貌,同时也会注意到不要因此冷落了在场的小姑子们,就说“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下面的话强调贾母对黛玉的宠爱和牵挂,“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但是,她也不会忘记,黛玉是因为丧母才来到贾府,马上又说:“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贾母笑责她这是招哭,凤姐又“忙转悲为喜”,连称自己“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这中间的情感切换是极为自然的。王熙凤讲话妥帖周全、滴水不漏,所谓“一万个心眼子”,在这数句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平日调笑间,贾母也很擅长拿捏分寸,只打趣可以打趣的人,从不做“交浅言深”的事情。在第五十四回中的元宵节晚宴上,众人在贾母的主持下玩起“击鼓传花”的游戏,按照规则,输了的人要说一个笑话。贾母讲的笑话是:一家子有十个媳妇儿,九个媳妇都不如最小的那个心巧嘴乖。她们感到不服,要到阎王庙去问个究竟。结果遇到孙行者对她们说,小媳妇之所以嘴巧,是因为托生时喝了他撒下的一泡尿。这个笑话说得很贴心,给了李纨等木讷嘴笨的媳妇一个打趣的机会。因为素来只有凤姐伶牙俐齿,在众人面前出尽风头,妯娌间难免有暗自不服者,认为贾母偏心。凤姐作为贾母跟前的第一“捧哏”,听完还故意说:“幸而我们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这时尤氏、娄氏、李纨等媳妇都道:“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连薛姨妈都说笑话妙在“对景就发笑”。可见,贾母对儿孙辈妯娌之间暗藏的龃龉、众人的想法都心知肚明。她知深浅、懂分寸,在阖家团圆的温馨场合用一个笑话轻松调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贾母虽然总是以慈祥和善、体恤下人的面目出现,但她对封建等级制度是坚决维护的,心中对主仆身份之别有着一条明确的红线。在第五十四回中,恰逢元宵节看戏,她发现袭人不在宝玉身边服侍,只有麝月、秋纹并几个小丫头跟着,便严厉地说,袭人“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儿出来”。听说袭人“因有热孝,不便前头来”,立刻反驳道:“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不成?皆因我们太宽了,有人使,不查这些,竟成了例了。”说完这些,才问起袭人的妈是什么时候去世,是否给了银子发送。从这些恩威并施的细节就能看出,贾母管家时期的贾府一定是等级分明、规矩森严的,暗合了贾敏曾告诉过黛玉“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的大家气象。
在任用凤姐管家这件事上,也能体现出贾母过人的识人之明。作为大家族里辈分最高的人,她需要在选人、用人上做决断。这是一件有大学问的事情。大儿媳邢夫人贪财鄙吝,唯贾赦之命是从,如果将贾府交到她手中,早早就会被贾赦败光了根本;二儿媳王夫人也管过事,但并无足够的理家才干;大孙媳李纨性格安静,为人宽厚,丧夫之后不宜抛头露面。所以贾母敢放手让年纪轻轻的凤姐管理荣府,这并不是因为王熙凤伶牙俐齿、会哄自己开心,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考量的。
贾母看重王熙凤什么呢?是她在应对家务事上的洞察力和行动力,也就是不用多做指示就能把事情办好的能力。比如在第五十一、五十二回中,因冬天里天寒日短,凤姐提议在大观园中另设一间小厨房,免去姊妹们为了吃饭,从园中跑回府里的劳苦。贾母非常赞同这项提议,说自己早就有这样的心思,但怕说出来给办事的人添负担,让这些当家奶奶们觉得自己“只顾疼这些小孙子孙女儿们,就不体贴你们这当家人”。为了这件事,贾母专门在王夫人、薛姨妈和前来请安的邢夫人、尤氏等所有媳妇面前夸赞了王熙凤,说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凤姐这样考虑周到。
情商极高的贾母,被薛宝钗称为贾府中最“巧”的人。在第三十五回中,凤姐想趁宝玉挨打想喝“莲叶羹”的机会,拿官中的钱做人情,被贾母当场点破。这时宝钗便当着众人的面笑道:“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这个“巧”字怎么理解呢?首先是会办事、做事考虑周到;其次是会说话。这两样都是王熙凤的“当家本领”,但贾母却要比凤姐更胜一筹。较之于凤姐,贾母的智慧在于她行事果决,但又不会过于显露锋芒,看似隐退幕后,但对头绪繁多的家族事务却能面面俱到,一眼看出其中的关窍,在人际关系的周旋中能全身而退。
这部小说的第二个前身是《红楼梦传奇》。“传奇”是当时对戏曲文体的指称。这部传奇可能并未完稿,只填了曲子,没有用宾白连缀起情节。但这些曲子没有被浪费,而是成了“作者自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耳”的总纲,作为寓言被穿小说之中。除了第五回直接名为“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外,书中写到的很多支曲可能在这部《红楼梦传奇》中也有其原本的位置。比如《好了歌》是借甄士隐之口喻唱贾宝玉悬崖撒手、弃家为僧;宝黛相见之时,书中为他们一人写了一首曲子,也有可能是在戏曲中介绍人物时所唱;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在冯紫英宴席上作了一首《红豆曲》,从内容来推测,它有可能是戏曲中黛玉死后,宝玉怀念她时所唱的曲子。
这部小说的第三个前身是《金陵十二钗》。曹雪芹在构思出《红楼梦传奇》之后,发现这部以宝黛钗爱情悲剧为主线的传奇故事还不足以囊括他全部的创作思考。他认为,自己在前半生于闺阁之中结识的那些女子,“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她们虽然性情、才干各有不同,最终的命运竟都归于悲剧。于是,曹雪芹将笔锋从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悲剧,扩大为一代贵族女子的普遍悲剧,构思出“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故事。《红楼梦》第一回中自叙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到《金陵十二钗》成形为止,《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初稿已初具雏形。
但《金陵十二钗》并非我们今日所见的《红楼梦》。己卯本第三十八回中有夹批提到:“看他忽用贾母数语,闲闲又补出此书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钗》的一般,令人遥忆不能一见。”有研究者据此解读,《红楼梦》之前或有一部题为《十二钗》的作品,但此书似乎并未完稿。甲戌本卷首提到:“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夹批中有云:“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盖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义。”也就是说,《金陵十二钗》的书名对应的是《红楼梦》曲中的十二钗,但远不能概括后来《红楼梦》书中出现的所有女子。
十二钗的命运不足以概括曹雪芹人生中的全部见闻。尤其是从贵族沦为平民之后,他的社会阶层、生活环境、视野见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沉到人民当中的曹雪芹对此前的生活有了更为深刻的省思,对不同阶层中的人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理解与同情。因此,局限于闺阁生活的《金陵十二钗》远非曹雪芹写作的终点。他最终将这部小说扩大到描写整个封建社会从上至下所有青年女性的悲剧命运,涉及正册、副册、又副册如此庞大的人物体系,以及许多来自市井、乡村,同样闪烁着人性光芒的人物。
曹雪芹用一生写就了这部伟大的小说,他最终定下的书名应当就是《石头记》。从贵族到平民,从“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他体验过各种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洞明世事、练达人情,提高了认识、积累了学问、凝练了文章。这个时候的他,既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又积累了多次创作经验。他把自己比作“无才补天”的顽石,将自己的生活比作顽石幻形于人世的经历,将早期作品《风月宝鉴》《红楼梦传奇》《金陵十二钗》等作为创作素材,方才写就一部前无古人的作品。
因此,《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也可看作曹雪芹思想的蜕变过程。这部小说采用多主题的复调模式,线索繁复、人物关系复杂,宛如一首宏大的交响曲。这样一部长篇巨著并非一朝写就,而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方才呈现出如今的样貌。也正因如此,《红楼梦》中留下了一些没有完全融合的情节,比如秦可卿的故事写得烟云模糊,而她或许本是《风月宝鉴》中的人物。因此在阅读《红楼梦》时,我们可以注意那些似断实连的节点,去探寻这部小说生成过程中留下的谜团。
通过对《红楼梦》多个书名的辨析,我们也可以学到一种思维方法:通过书名来了解一部小说的生成方式。这种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经典名著。如果一部经典作品有着不同的书名,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不同书名去探究小说的创作、传播、接受过程。比如《西游记》写的是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这本是唐初的一段史实,《旧唐书》《唐高僧传》等史传中都有记载。玄奘将他在此行途中的见闻写成了一本《大唐西域记》,书中并没有介绍西行的路途有多艰险,强调的是对“西域”风土人情的记录。后来玄奘的弟子将他的事迹写成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重在赞颂三藏法师的求法之心何等虔诚。至宋元时期,在民间说经讲唱人的翻述之下,出现了一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这部面向普罗大众的作品中,故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神通广大、擅长幻化的“猴行者”。到了元杂剧盛行的时代,出现了很多以“西游记”为题的戏剧本子,将师徒四人曲折神异的“西游”故事搬上了舞台。有了这些前期的素材积累和故事变化,到了明代中叶,我们今天熟悉的小说《西游记》才终于呈现在读者眼前。由此可见,一部小说的书名很可能隐藏着它的创作过程、主题演变和接受过程。
《石头记》设定了一个石头下凡的大框架,为小说勾连出神话传奇的故事背景;《情僧录》包含着“自色悟空”的佛教思想,提示我们关注书中寄寓的理性与哲思;《风月宝鉴》点出沉溺风月是家族衰落的根由,突出了小说的世彩与现实意味;《金陵十二钗》突出的是女性的悲歌与赞歌,提示我们以女性小说的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红楼梦》的书名则总而括之,突出“南柯一梦”的繁华与荒凉色彩,具有强烈的兴亡演替寓意。这五个书名是我们理解《红楼梦》丰富、多元思想意蕴的关键。
楔子中交代了《石头记》书名的来历:青埂峰上无材补天的石头遇到一僧一道,听他们谈到红尘中的富贵繁华,便一心想要“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它苦求再四,被夹带在神瑛侍者下凡历劫的公案中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当它回到青埂峰,变回石头原形时,身上已写满字迹,记录了在人间的经历。后来又经过不少岁月,被偶然路过的空空道人抄录,才有了这篇《石头记》。在这段叙述中,作者没有写到石头在人间经历了什么,只交代了本书的叙事视角——整部小说的亲历者与记录者是这块顽石。
《情僧录》是神话故事与现实之间的过渡,具有强烈的宗教隐喻。这个名字既能令人联想到空空道人所在的仙凡之间的世界,也隐喻着顽石落在贾宝玉身上,在人间以情悟道的历程。空空道人是这篇石上文字的抄录者,也是这篇文字的第一位读者,他通过阅读石头的经历,“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成为“情僧”。此处寄寓着一重隐含宗教色彩的题旨:世人或像贾宝玉一样经历盛衰荣辱、世态炎凉,或像空空道人一样通过阅读小说领会其中真意,才能勘破迷障、了悟解脱。
《风月宝鉴》的书名寄寓着作品对世情风月的省鉴和反思。书中与风月有关的笔墨,如贾珍与秦可卿,薛蟠与香怜、玉爱,秦钟与智能儿,凤姐与贾蓉、贾瑞,贾珍、贾琏与尤氏姐妹,贾琏与鲍二家的……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大观园外,与大观园干净清洁的女儿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部分情节或有借鉴曹雪芹早年创作的《风月宝鉴》,而被嵌入《红楼梦》家族兴亡的大格局之中,成为“家事消亡首罪宁”的具象呈现。这种“嫁接”和“移植”,隐含着曹雪芹对家族命运的深刻反思。
《金陵十二钗》则对应着大观园内的女儿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同样存在明清小说中的传统母题——“情理之辩”。薛宝钗和林黛玉分别隐喻着封建贵族女性的两种人生范式——理性精神的规训和才情性灵的高扬。薛宝钗是被礼教规训出的标准“淑女”,一言一行处处体现着“理”对女性的规训与要求。在她心目中,“情”必须让位于“理”。而林黛玉则相反,她终生与诗书为伴,因情而生,为情而死,以“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决绝对抗礼教和世俗对女子的规训。黛玉身上有《牡丹亭》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杜丽娘的影子。钗黛二人及她们身后的副钗、又副钗,代表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两种审美理想——“闺门之秀”与“林下之风”,也隐喻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生道路与价值选择。
《红楼梦》的书名则令读者联想起第五回中贾宝玉的幻境一梦。他在梦中看到了十二钗判词,听到了隐喻着十二钗未来结局的命运判曲,却仍未悟出曲词内容写的是自家事。在梦中,他被可卿教授云雨之事,春梦却忽然化作噩梦,陷入迷津。太虚幻境的梦境隐喻借鉴了“黄粱一梦”的文学传统,这种故事在唐传奇、元明戏曲中比较流行,如唐传奇中有沈既济的《枕中记》、张的《游仙窟》,元明戏曲中有《南柯梦》等,讲的都是梦中繁华终为虚幻的道理。
宝黛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重要的构成部分,但这条线索只是整部书的一部分。从开卷第一回至第十七回,基本上都没有提到宝黛爱情,写到两人相处的场景,只有第三回“宝黛初见”、第七回“送宫花”、第八回“金玉相逢”和第十七回“黛玉误剪香囊”。而通过书中判词、诗文及评点的暗示,可以推测出黛玉在全书结束前便夭逝,在她死后还发生了一系列事情,种种情节设定都远远超出了宝黛爱情的题旨。《红楼梦》塑造这两个人物,绝不是才子佳人小说中围着爱情打转的角色。小说赋予了他们各自独立的人物成长线,表现他们对人生、对命运逐步深入的思考过程。
从小说架构上看,《红楼梦》至少包含着三个层次的悲剧:一是仕宦阶层个体出路的悲剧,以贾宝玉在爱情和人生道路上与世不容、四顾无路为代表;二是女性群体的普遍悲剧,以“金陵十二钗”等所有女性在封建礼教制度压抑下葬送美好人生为代表;三是封建贵族阶层坐吃山空、后继无人的历史悲剧,以贾府的败落和衰亡为代表。像贾府这样的封建贵族阶级为了“冠带家私”相互倾轧、争夺乃至陷害,从内部开始崩塌瓦解的命运,也预示着整个封建制度摇摇欲坠、分崩离析的历史悲剧。
细读这套《红楼梦曲》,会发现曲文多采用第一人称,如元春判曲《恨无常》中的“儿命已入黄泉”,探春判曲《分骨肉》中的“奴去也”等。这种写法在明清传奇剧本中很常见。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判曲可能是角色唱词,用来抒发剧中人对自身命运的感叹。此外,还有一些曲子采用的是第三人称视角,比如秦可卿判曲《好事终》,很像秦氏去世后,旁观者对宁国府的谴责。《引子》和《飞鸟各投林》则像一部传奇剧的开场曲和终场曲。所以有研究推测,第五回中的《红楼梦》曲或许源于一部有完整构思的传奇剧本。